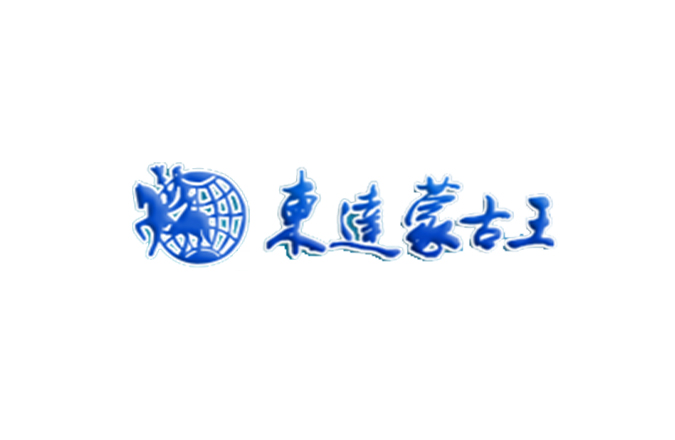绿色鄂尔多斯不解的沙漠情缘

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吉格斯太镇乌兰壕村,天高,云淡,风清,绿色绵延。
站在高处极目远眺,依稀还能见到黄沙的影子:它静卧在那里,与绿色相伴而生。
这里上演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与沙的爱恨情仇。
上世纪50年代,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,连绵起伏。有时黄沙在风的怂恿下,将天地连成一片,将人围困。一夜之间风推着沙包围了房子,掩埋了庄稼,吹毁了道路。人们在此深受其害,出门眼睛睁不开,在家推不开门。风沙每来一次,都会制造混乱:人们辛辛苦苦种的几亩口粮一夜之间化为乌有,人们咒骂着将院子里的土铲到外面,将埋没的道路清扫出来,人们对沙漠有捶胸顿足的恨,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奈,很多人被黄沙“欺负”得外出谋生。
乌兰壕村的蒙古族汉子白永胜一个简单的想法改变了人和沙的境况:1958年他随父辈来到乌兰壕放羊,有一天晚上在沙漠里迷了路。他想,如果能种几棵树,就能找到家了。当时不知道沙漠里该种什么树种,恰巧有亲戚从甘肃带来了沙柳苗,白永胜把沙柳苗种在房子的四周。一年后,绿色的沙柳围起了庭院。但因此,白永胜被认为是“想当林主”戴上了“私自栽树”的帽子,受到了批斗。明着不行暗着来,晚上他偷偷地到沙堆上种沙柳,然后再用沙蒿枝盖上。
那点点的绿色让村里的人看到了安家护院、抵挡风沙的好处。人们跟着白永胜试着在沙里寻找生存之路。他们从几十公里远的展旦召拉回沙柳,没有公路,没有汽车,就用牛车、骆驼拉,冬天把沙柳运回来集中到有井的地方,给沙柳洒上水,防止沙柳干死。春天的时候,人们一捆捆背上沙柳进沙,举步维艰地爬上一座又一座沙丘,甚至背上干粮住在沙里。有时春天栽上,夏天就被风刮起来,要不苗随着沙丘流走了。乌兰壕村人在沙里“投资”了一代人,终于,村庄有了丛丛簇簇的绿色,种植的沙柳还解决了人们没有柴烧的难题。
沙漠里依旧经常卷起风暴。
“种树种草,谁造谁有,允许继承流转,打破界限,长期不变”,80年这一政策极大调动了人们的种树种草积极性。积木成林,经过几十年两代人在沙漠里摸爬滚打,乌兰壕村占地约13万亩,有林面积9万多亩,包括沙柳7.5万亩和乔木2.2万亩。一个沙漠腹地的村庄森林覆盖率竟然达到80%!在与沙漠你进我退、你退我进的纠缠中,昔日黄沙变成绿洲,黄沙之下,根系纵横交错,将黄沙紧紧抱住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我们就是靠沙吃沙。”村民王来生说,他们靠沙柳挣了40多年的钱,靠沙吃饭,靠沙培养子女,靠沙致富。
乌兰壕村雨水匮乏,土地贫瘠,风害严重,人们连生存都非常困难。大集体时期,王来生还清晰地记得为了生活,一家人偷偷捋白条(沙柳苗条去皮,用来编筐)的情景。晚上点煤油灯,怕被人发现,将门窗堵得严严实实。一斤白条3毛钱,卖了钱欣喜得不得了,这是“救命的收入”。
白永胜靠卖树得来的钱给五个儿子娶了媳妇,他说:“没有挣钱的本事,这些树可是帮了我大忙,要不是这些树,我五个儿子不是要打光棍?哪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?”
村支部书记李文玉的几个孩子就是靠沙柳培养出来的。孩子2000年考上大学,家里没有一分钱,春天上学去沙里割春条,攒起路费学费,秋天又在沙里割秋条,到开学正好攒足学费,踏踏实实送孩子上学,年复一年。
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也是出生在沙窝子里的企业家。2010年在他提出“生态建设不以绿色划句号”理念引领下,将生态建设与林沙产业作为“二次创业”目标,总投资5.8亿元,建成了全国首家年产15万立方米沙柳刨花板项目,为沙柳找到了出路,把沙漠变成了新的财源宝地。
乌兰壕村因种沙柳而闻名,这里沙柳数量多,集中连片,有良好的开发价值。经过实地调研,东达林沙产业刨花板厂在乌兰壕村建了沙柳收购点。企业平均每年在乌兰壕村收购沙柳4000多吨,全村因沙柳获利百万元。沙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金棍棍”。
葛丑是乌兰壕村的种沙柳大户,他从80年代末开始种植沙柳,贷款种沙柳,一次性种了1000亩沙柳,陆续植起3000亩林地。从每年冬天11月到第二年春天4月整村的人就在沙里割沙柳。沙柳需要每3-4年平茬一次,平茬复壮。冬日里,葛丑两口子开上三轮车带上干粮进沙,从上午9点钟到下午3点钟,当日把割下的沙柳卖掉,收购点不拖不欠,他们当即就能拿到400多元的纯收入。一年下来,仅沙柳一项就收入3万多元。“沙柳是乌兰壕的强项,我们的沙柳后辈儿孙也砍不完!”村支部书记李文玉高兴地说,“全村有三分之一的收益来自林业,现在就连老年人也干劲十足。”
是沙柳养活了乌兰壕人。“以前这沙可是害人了……”“罪都让上一辈人受了,前人种树,我们后人乘凉啊!”“沙柳长得可好了,大沙柳有两三米高,一排排的像一堵墙一样……”这片沙记载了乌兰壕的故事,承载了乌兰壕人的情感。
耳畔有嘶嘶的风声,但再不会有风沙打脸。乌兰壕人与这片沙、这片绿和谐共处。
(高玲)